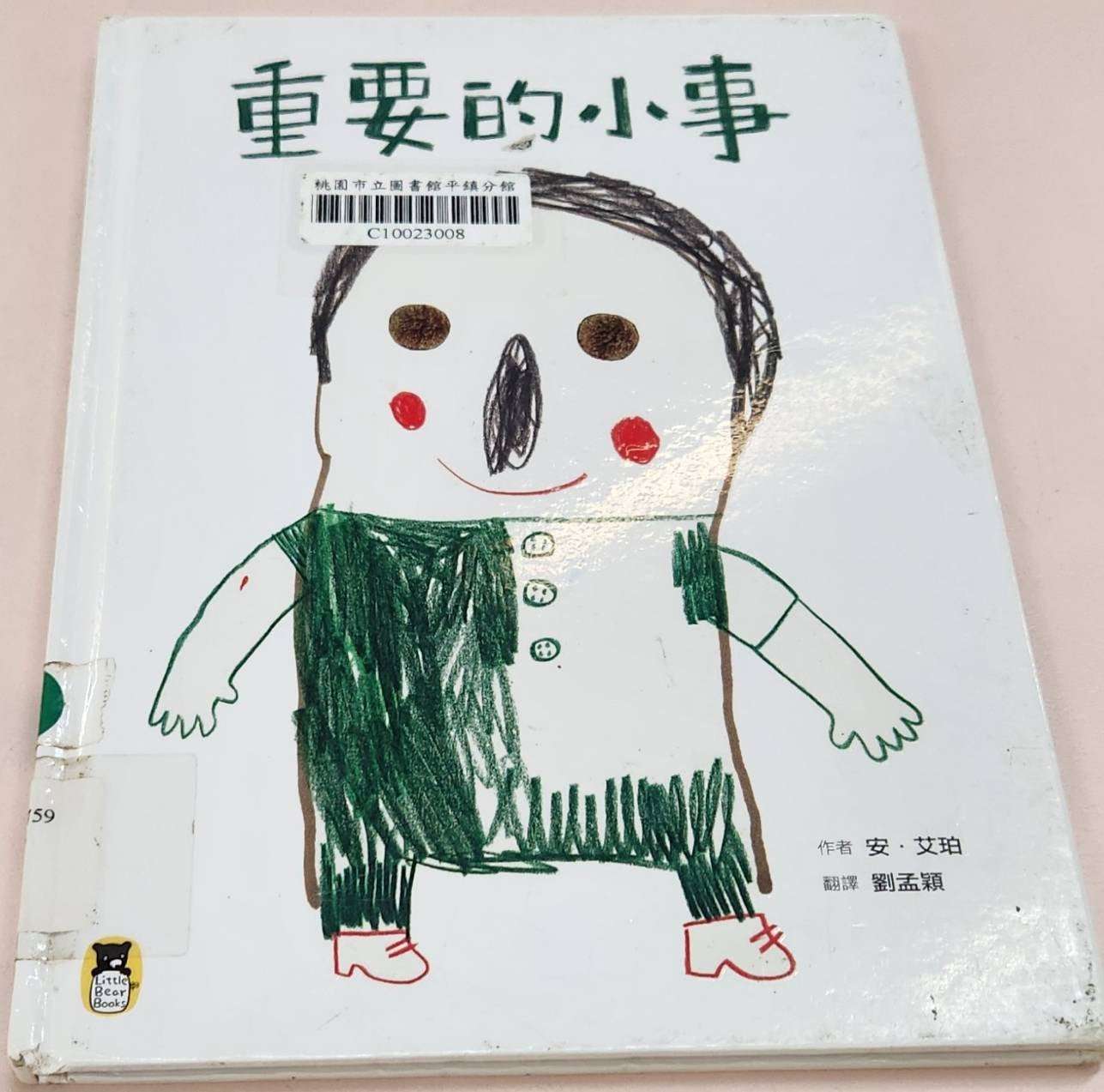- 粉圓,一個極具台灣特色的食物,這本書是吉本芭娜娜特別寫給台灣讀者的禮物。
- 「人生僅此一次,還是盡量過得幸福比較好;還是盡量與心愛的人,開懷享受美食比較好。
- 」--吉本芭娜娜《惆悵又幸福的粉圓夢》。
- Q:這篇在講什麼?
- A:粉圓,一個極具台灣特色的食物,這本書是吉本芭娜娜特別寫給台灣讀者的禮物。
- Q:重點是什麼?
- A:「人生僅此一次,還是盡量過得幸福比較好;還是盡量與心愛的人,開懷享受美食比較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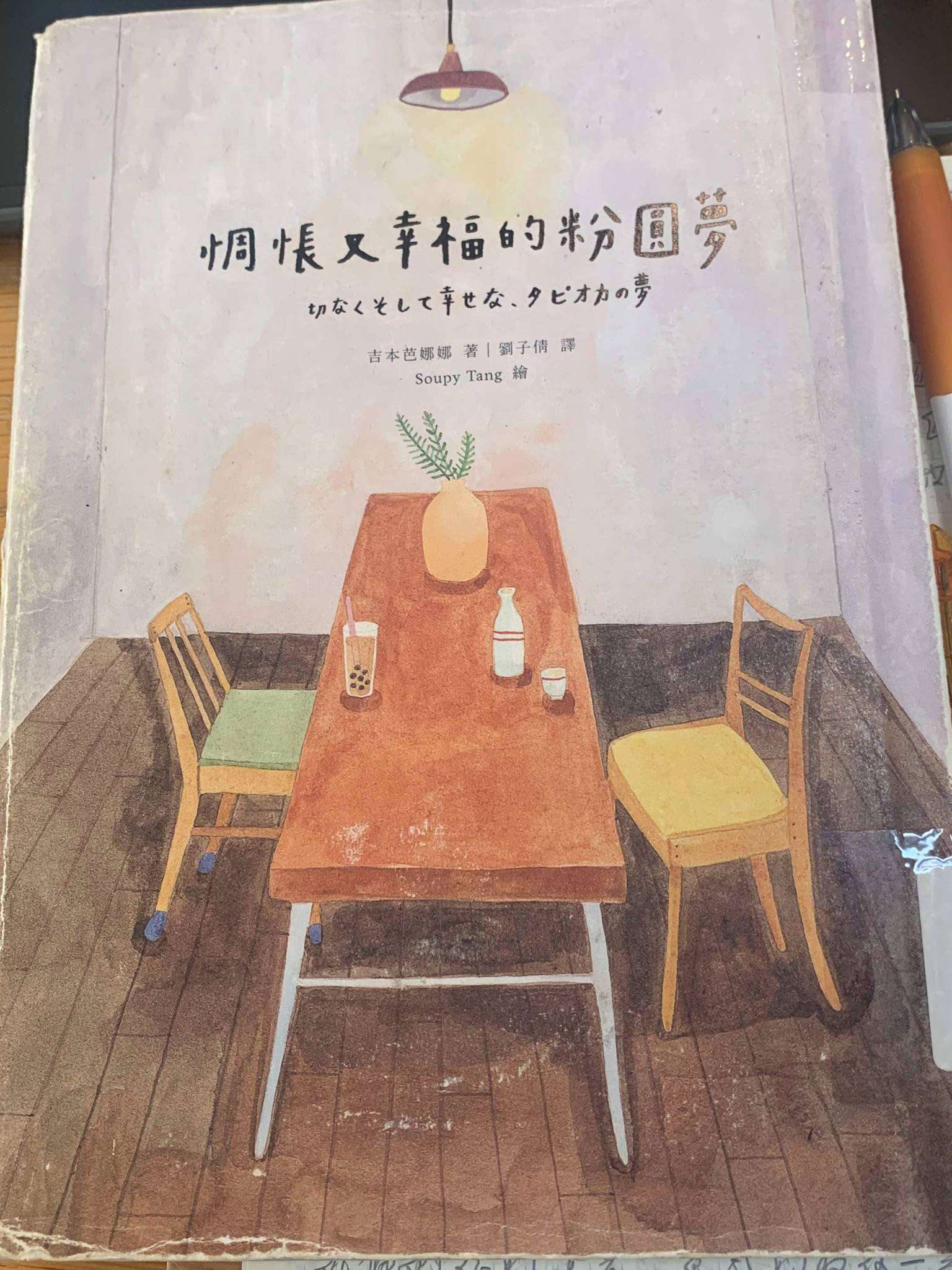
「人生僅此一次,還是盡量過得幸福比較好;還是盡量與心愛的人,開懷享受美食比較好。」--吉本芭娜娜《惆悵又幸福的粉圓夢》
假日的圖書館裡,離閉館時間只剩一個小時,我寫完了這週的觀影心得、抄錄整理好兩本書的閱讀紀錄、日語文法筆記的學習進度也已完成,而自己帶來的書我已不想讀了(帕慕克《別樣的色彩》一書後半的主題牽涉太多土耳其的政治歷史,讓我讀得心不在焉)--剩下的這一個小時適合做什麼?適合去書架上找本一個小時內可以看完的書。
我從書架上取下吉本芭娜娜的《惆悵又幸福的粉圓夢》,不但在一個小時內看完,而且看了兩遍;不但看了兩遍,還在抄錄整理好閱讀紀錄後,仔細欣賞書頁裡搭配文字,一幅幅台灣插畫家湯舒皮畫的色澤溫潤、畫面溫馨的插圖。
這本小書,讓我重新確定一個我很久以前妄下的論斷(不見得準確,但值得一試):如果你很喜歡某個小說家,那麼一定要看他寫的散文,你會更喜歡他;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小說家,請試著去看他寫的散文,應該會覺得比他寫的小說更好看。原因可能是散文比小說更接近作者「這個人」,較容易看到他的日常生活、脾氣性情、習慣喜好、生命軌跡,簡單的說就是:散文裡的小說家比較像自己的朋友,儘管作者根本不知道我這個自以為是裝熟的讀者是誰。
喜歡吉本芭娜娜這個小說家嗎?我曾經以為我會喜歡。年輕時跟著當時出版社帶領的風潮讀了幾本她的小說,如同所有熟知她的讀者一樣,我們都沒有錯過《廚房》這本書。但隨後閱讀另外幾本她早些年的作品,總覺得主題故事與表現手法,都不出《廚房》的風格與模式:多半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失去,主角在無可掌控的情節發展下,讓那些看似尋常清平實則複雜難明的心情反覆迴繞,有時故事裡夾雜某種迷惑的異樣元素,也許是紛亂詭異的夢境,也許是有特殊身分或奇妙能力的角色,總之最終他們總會找到繼續走下去的方式。這樣的故事不好嗎?不是不好,也許對當時的我生命歷練還是太少,總覺得這些故事少了一些明確的現實感,當我企圖在書中找到療癒的力量時,感覺希望之光過於微弱而不可恃。
二十多年後,在某個契機下我十八歲的學生將他珍藏的《廚房》借給我:「老師,這本書妳應該會喜歡。」我接過書時沒有告訴他我曾經以為我會喜歡的,但是……,為了不辜負他的分享,我重看了一遍書裡的故事。
也許是年紀增長了,也許是心境不同了,這一次我在故事裡讀出了吉本芭娜娜這段話想表達的意思:我想把自己切身感受到的「過於敏感帶來的苦惱與孤獨,的確有其殘酷的一面,幾乎難以忍受。但是只要還活著,人生就會繼續走下去,那肯定不是甚麼壞事。就算纖細易感,只要善加利用那個特質,還是有可能快活過日子。因此最好放下天真的心態,對自己的傲慢有所自覺,培養冷靜的態度。只要下點功夫,人肯定可以隨心所欲地活著」這個信念,獻給經歷各種痛苦悲傷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心靈荒蕪,正渴求外界滋潤的人。
因為讀到這段話,吉本芭娜娜從小說家變成我的朋友(儘管她根本不知道我這個自以為是裝熟的讀者是誰),於是在這樣一個下午,我從圖書館的書架取下了「朋友」的《惆悵又幸福的粉圓夢》。
書裡透過一個個與食物相關的小事,平凡家常得如我們每一個人家中會出現的的場景,串起她與家人情感相連的回憶。外人如何逐漸成為家人?那種自然熟成的過程,吉本芭娜娜用發酵來比喻:「時間如同美味的醬菜或對胃腸有益的優酪乳,為我們的關係帶來發酵」。累積一次次一同享用佳餚美食的機會,讓我們的情感發酵出醇厚濃香的氣息,鑲鐫在記憶中,隨時等待召喚。
吉本芭娜娜至今仍記得兒時與父親至市場採買後,手裡抱著菜蔬坐在車子裡看家鄉街頭雜亂無章的街景;記得父親用竹輪麩代替烏龍麵的獨特味道;記得父親的菠菜大全餐和道道都加了奶油的料理。長大後她若想喝以前父親煮的濃如味噌醬的味噌湯時,她便會學父親將蘿蔔切成絲放入湯裡,而這種切絲不切塊的方式,想必爸爸的媽媽,她的奶奶也是這樣切蘿蔔的。我們留在記憶裡的不只是家族料理的味道,還延續了食物的烹調方式。
當她成為母親後,連結著和小小孩手牽手去超市記憶的是黃昏酒吧裡氣泡葡萄酒和紅肉甜橙汁的味道。「媽媽的番茄湯真叫人懷念!」這味道成了兒子人生中無法忘卻的一部分,她對自己創造出這種東西感到不可思議。
想起你的時候也同時記起你為我做的料理、我為你準備的食物、我們一起享用的美味,多麼的幸福!幸福,卻也惆悵。當吉本芭娜娜意識到長大離家後的孩子空蕩的房間裡,不會再傳來他用力吸粉圓的吸吸簌簌,刺耳又沒規矩的聲響時,她看見人生歲月流逝的具體模樣,「想必叫人惆悵吧」她說。
但正是歲月給了我們累積與所愛的人一同吃著餐食的機會,我們才能在時間流逝後去感受去品嘗去回味這樣的惆悵啊!《廚房》裡雄一對美影說:「為什麼和你一起吃東西,好像就覺得特別好吃?……肯定是因為我們是一家人。」有幸能在一起吃飯,吃久了,就會成為真正的一家人,就算日後無法在同一個時空裡共享美食,想起時會即使感到惆悵,但還是幸福。願我們都能擁有這樣的幸福。
作者
郭淳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