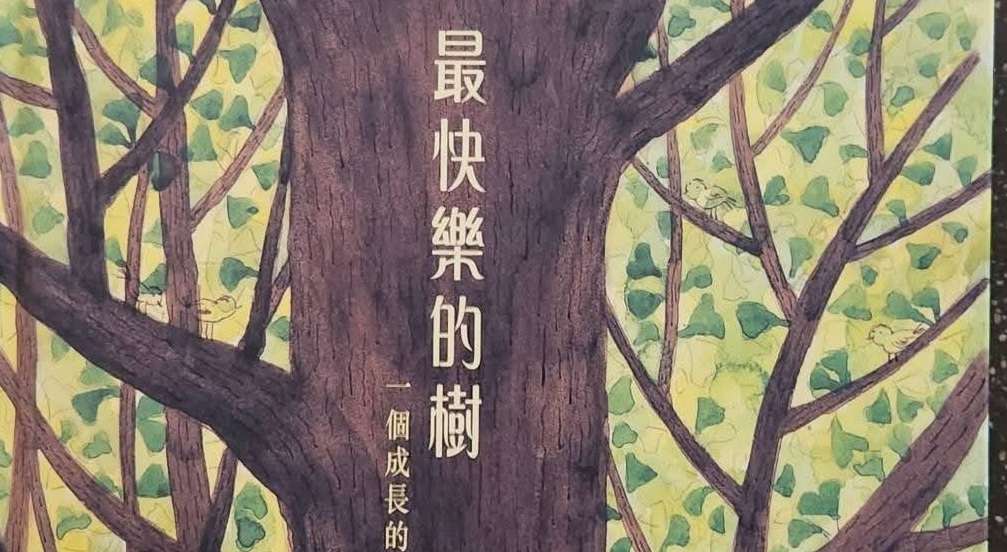- —讀梁峻瑋隨筆〈再見了,雙和醫院〉—。
- 高明的作者,經常地思索,長期地浸淫在他生活中經心和不經意兩端裡的,會在其字斟句酌或看似簡單不過的鋪述上,共同參宇宙之造化(上下四方謂宇往古來。
- 史遷年方二十壯遊,踏尋諸多地域,這些他足跡所至之處及他探詢各地耆老、親聞相關人士與後裔子孫的口述史料,難道不是在那般年紀時,胸中早存點墨。
- Q:這篇在講什麼?
- A:—讀梁峻瑋隨筆〈再見了,雙和醫院〉—。
- Q:重點是什麼?
- A:高明的作者,經常地思索,長期地浸淫在他生活中經心和不經意兩端裡的,會在其字斟句酌或看似簡單不過的鋪述上,共同參宇宙之造化(上下四方謂宇往古來。
—讀梁峻瑋隨筆〈再見了,雙和醫院〉—

高明的作者,經常地思索,長期地浸淫在他生活中經心和不經意兩端裡的,會在其字斟句酌或看似簡單不過的鋪述上,共同參宇宙之造化(上下四方謂宇往古來今云宙),前文提及的「下潛至無意識的自然流洩而出」,星星點點的漁火實則也是辛勤忙亂的漁人與魚群的對峙,裡頭或也有經常性「流水性機械化」的動作,〈蘭亭序〉「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高明的作者自亦能:吾之視人,亦猶人之視我;吾之視物,物亦以之應吾。
史遷年方二十壯遊,踏尋諸多地域,這些他足跡所至之處及他探詢各地耆老、親聞相關人士與後裔子孫的口述史料,難道不是在那般年紀時,胸中早存點墨!終到人生將屆結束前,完成參天地造化成一家言的史學鉅著《史記》的內涵。全書的大格局結構,早有了規劃的芻形?愛因斯坦為世人所知的諸多現代物理學理論,連一般人文學科學子都能粗曉其基本原理,如狹義、廣義相對論,普朗克-愛因斯坦關係式,……重力波,……,古典統一場論,其實,在他就讀蘇黎世大學前後階段,均已然在其「物理想像」中隱然成形,而後的生命歳月,則逐步成形,一方面彼此挽結成一系統,一方面有待實證物理學去證實其理論的存在。
梁峻瑋先生這篇隨筆,如此獨特性的睇視,依作者書寫,實飽含著「元質樸素」的導航特色待識見與夫完實:筆者以為,恰是源自於他深諳「物理時間」與「人文時間」,交互作用於創發性的思維上,致使美的意向不再停留在單純的繪形、寫意:
1「遠近漁船作業,星星點點的燈火在氤氳之間-下弦月先是依傍著山勢,攀附,猶疑,最終沉入了基隆山後頭」
2「泛起圈圈的光暈向外擴散-湧動的雲絮卻因為這不可見的光亮」
3「在幾無路燈的路段,成為絕對的夢幻-從山後延展出詭祕的色澤」
截取梁先生文章,自然造成閱讀完整性之中斷,實不得不為之舉:「只有經過誠摯懇切的分析,唯有分析,才能期勉做出適切的評論」,這是評析者基本的自我要求。
前文已然述及,這是梁先生的隨筆書寫,何以筆者如臨深淵般肅然以對—敬—
這三組,本然狀態處在兩處完整的對外界變化的述寫描繪,第二處伊始的「轉身」,極具隱喻的象徵,前處1是遠眺平視的點點漁火:人文活動,對遠眺者是某種渺浩閒曠情懷,帶舒解自身亂離惶憂情緒作用;對一艘艘竄入闃黑深邃冒生命危險作業的漁人們,則彷如身處戰場,哪來優閒?其世界的空間時間,是交織進自然空間裡的人文時間(有趣的是作者是由人文時空的蹙囧,求索某種舒放,去哪都好,成了身體無意識的:去最能療癒的好地方,勢必然的選擇而闖入人化的自然時空)如漣漪般外拓的漁火光圈,與對映成趣的無光路段,讓我腦海中浮現不少如此的畫面,只舉一例,「霍爾移動城堡」將結束前的尾聲,女主蘇菲藉由霍爾交付予她的戒指射出指引的光,走進男主霍爾的心界—內心世界—,方得以邁開步伐,在原本闃黑黯黝的世界裡走出一條路。這樣的畫面,不論用甚麼手法描寫,都(所以有情之人人皆有感)會有絕對夢幻之情油然升起。
轉身後,空間與時間的運作者,是下弦月,是基隆山頭,是浮動的雲絮與夫詭秘的色澤,這兩組對照是豐贍具漾散效果的:讓筆者先行交代清楚:123;1前1後,2前2後,3前3後,這是十分淺陋的二元分析,讀者請留心,這樣的分析只是先求一目瞭然,而真正的訴求是「交織出入」:轉身前,是從繁雜亂離的人文世界逃出,而轉身後是自然物象時空(無論如何終歸得人化)的世界,其源質能量當然是筆者所示的「凝睇」。
一純然人文世界(人類打造的生活時空與模組),擁有獨特凝睇的心靈,轉換心象提升對世界的感知,化人文意象時空融入人化的自然時空意象世界,創造性的再一次提升的時空世界,成為交織匯通了「饒富滋味的『新』」的世界時空……
像極了進行解抗阻的心理師——「架好腳架,我拍了一個四分鐘的長曝光。」
這個行動本身只是梁先生諸多興緻終成為獨特能力的其一。當然,有滋味的是,這也與筆者所下標題「凝睇」有直接關連,梁先生的目光是多歷年所打造的火眼金睛,這個四分鐘的長曝光,對象不言可喻是他照片中的「陰陽海山城」,這裡同時共存自然與人文的時間空間,進入作者的照片世界中又轉而會成為恆久遠的自然人文交織的時空中的部分與整體(即自然即整體地即人文即部分)
鏡頭一轉。然後,人生,世界,就是這樣,聚散恍怳
浪花趕赴,湧起歡欣,碎裂,愁苦湧起,碎裂⋯⋯
用電腦複製,剪下,貼上,略做變動組合,人生就是這樣?
筆者不一定以為然,最饒富「漾蕩」……「展延」……「擴散」……原創性的部分段落,更成為這篇隨筆散記最富「樸素元質」性的,便在收束處現形:
釣客不動,蹲踞相機旁的我「也」不動,時間單位周期以數百萬年計的基隆山也不動;大江大海,雲蔚霞樹,浮漾翩躚浮移實則亦何曾有動……只是,釣客心動,我心亦不居,基隆山大江大海樹蔚雲霞,又何嘗不是於更深邃更袤闊及已可知與夫未可視的未來,移徙不定,偏偏必然如此。
高明的作者,他說「其間變動的,只有相機螢幕上倒數的秒數,以及耳邊往復來去的浪花,湧起,碎裂,湧起,碎裂」
高明的作者,他也說「我覺知所有的聚散,趕赴,歡欣或者愁苦,其實也就是這個樣子。人生也就是這個樣子。」
「人的身體是器,人的心是更大的器;器,有甚麼不好的,偏有人說,君子不器」那就讓我們涵養自身,甚且相信,人是最深具共感力的存在,涵育自己與夫能進到相同世界的他人—同於我不同於我皆能同於共感的他人—與天地參與宙宇器,當人可以量融於宇宙,這般的器如何不為,又有何不可為?
果然,這豈不是根本性的放棄人所以為人的獨特性與創發力?
作者:王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