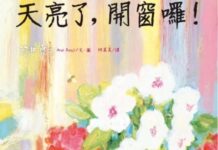- 圖:翻攝自Rakuten kobo。
- 派翠西亞・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的《火車怪客》,乍看是驚悚推理小說,不過對我而言,這部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對。
- 海史密斯筆下的謀殺,關於道德動搖、罪惡感與懲罰的意識,而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也將參與這場心理實驗。
- Q:這篇在講什麼?
- A:圖:翻攝自Rakuten kobo。
- Q:重點是什麼?
- A:派翠西亞・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的《火車怪客》,乍看是驚悚推理小說,不過對我而言,這部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對。

派翠西亞・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的《火車怪客》,乍看是驚悚推理小說,不過對我而言,這部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對人性陰暗與心理裂縫的深刻描繪。
海史密斯筆下的謀殺,關於道德動搖、罪惡感與懲罰的意識,而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也將參與這場心理實驗。小說提出一個駭人的構想:「交換殺人」。兩名素不相識的人在火車上相遇,若各自殺掉對方想殺的人,因為缺乏動機,警方幾乎無從追查。布魯諾提議幫蓋伊殺掉遲遲不肯跟他離婚的蜜莉安,蓋伊則是幫布魯諾殺掉他的父親。
然而,如果真正成功的謀殺在於「逍遙法外」,故事的張力便在犯行逐步走向「失敗」之處發酵。理論上,若要確保不被懷疑,兩名兇手在行兇之後應該澈底分道揚鑣。但布魯諾卻無法停止糾纏蓋伊,他一再靠近、盤旋,衝動難以言喻。
這種不合理的執著,不僅讓兩人陷入風險,更讓情節隱隱浮現同志情慾。布魯諾對蓋伊的依戀既像威脅也像誘惑,而蓋伊的態度則游移於抗拒與依附之間。在一個必須隱藏慾望的時代,小說把情慾與謀殺並置。
蒙田曾經指出,我們的內心往往同時存在對立的兩面:我們譴責的東西,往往也是我們無法擺脫的東西。蓋伊與布魯諾的關係,行動的反覆無常,此彼的雙重性正好可以呼應蒙田的洞見,將分裂的人心與思考具體化了。布魯諾是蓋伊壓抑慾望的替身,是他在社會秩序之外的另一種可能。陌生人漸漸發展為彼此的鏡像,無法分開。
布魯諾代表慾望的放縱與破壞,總是醉醺醺的,他不受倫理規範拘束,直接實踐了犯罪的可能;蓋伊則顯得壓抑,努力維持「體面」的生活,理想的幸福生活漸漸被布魯諾一步步侵蝕。看似對立,實際上布魯諾揭露了蓋伊內心深處想逃避責任的陰影,而蓋伊的掙扎又映照出布魯諾的偏執,他們的矛盾成就了小說的魅力。
小說後段布魯諾的墜亡,他的死亡究竟是醉酒意外,還是潛意識中的自我毀滅,文本並未給出明確答案。從此之後,故事失去了一極,僅剩蓋伊獨自承受。理想的友誼裡,朋友應該能分擔痛苦,但是因為犯罪而結盟的共犯,是排除了他人、獨享的關係,比朋友或兄弟還緊密,這種關係又該怎麼稱呼呢?布魯諾死後,蓋伊認識到先前布魯諾分攤了他一半的罪惡感,如今被湧上的罪惡感與懲罰意識撕扯,那麼誠摯的獨舞,告白罪行的渴望,讀者甚至開始不自覺地同情這位殺人犯,為他的焦慮與懊悔而憂心。
這正是海史密斯的高明之處,讀者也陷入了這場心理遊戲,我們聆聽兇手的吿解,同時被兇手的內心狀態所滲透,直到我們驚覺自己竟然在擔心一個兇手的處境,而最終那扇門終究必須打開。善與惡、秩序與混亂並非單純的對抗,而是因彼此存在而互相成全。如此,布魯諾與蓋伊的關係不僅是一場心理的對峙,更是人性內在光明與黑暗交織的具象化。
不過這裡要指出的是,布魯諾與蓋伊的關係並不是單純的由誰來代表光明與黑暗,別忘了他們都是兇手,他們終將是無法分開的「連體嬰」。讀者在厭惡布魯諾的偏執與暴力、同情蓋伊的掙扎時,也不得不察覺,兩人合在一起,正揭示了某種更廣泛的社會現象,尤其是男性暴力在社會秩序中被遮蔽或合理化了的事實。
《火車怪客》的閱讀過程令我體驗了心理與倫理上的波折起伏。誰都可能殺人,海史密斯揭示了謀殺潛伏在每個人心底,沒那麼遙不可及。理性與慾望、秩序與失序、抗拒與依附,甚至愛與罪,都在蓋伊與布魯諾的鏡像關係裡糾纏,包括死者的永恆沉默也滲進我們的內心深處。
作者/傅淑萍
現為「我們的教學事業有限公司」講師,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部落格「樂遊原」與IG「樂遊原(@leyou_yuan)」共同經營者。曾任聯合報文學寫作營講師。曾擔任聯合盃作文大賽閱卷與命題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