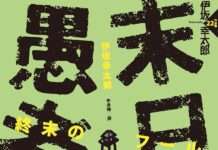- 圖:翻攝自Rakuten kobo。
- 選擇以魔法為背景的小說不少,匡靈秀的《巴別塔學院》,以及她的新作《地獄修業旅行》都屬於魔法世界。
- 魔法的核心是語言,語言的意義依附於它被使用的社會情境,因此,除了欣賞魔法帶來的冒險與奇觀,從語言如何被運用並塑造現實的角度來看匡靈秀的小說,。
- Q:這篇在講什麼?
- A:圖:翻攝自Rakuten kobo。
- Q:重點是什麼?
- A:選擇以魔法為背景的小說不少,匡靈秀的《巴別塔學院》,以及她的新作《地獄修業旅行》都屬於魔法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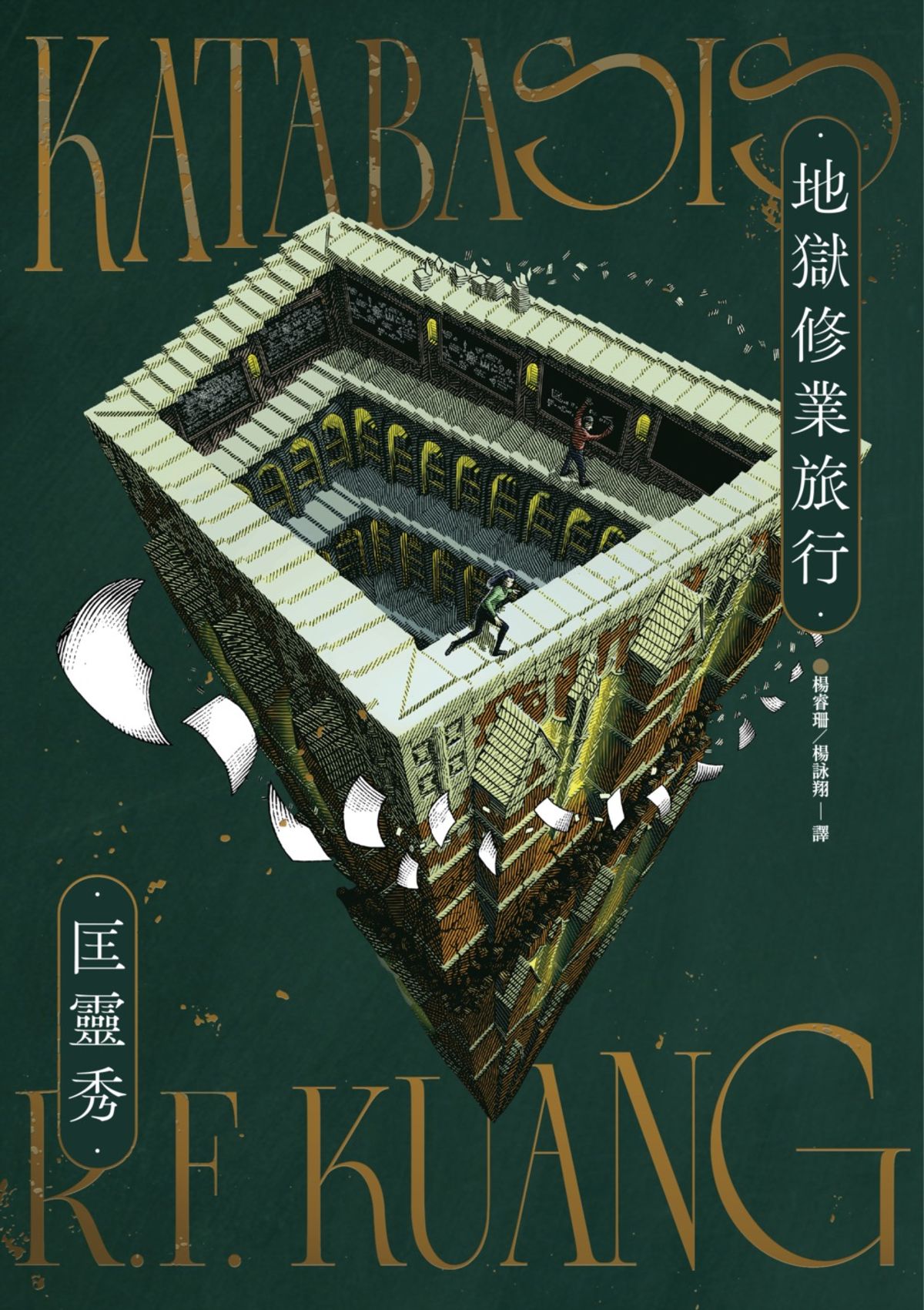
選擇以魔法為背景的小說不少,匡靈秀的《巴別塔學院》,以及她的新作《地獄修業旅行》都屬於魔法世界。魔法的核心是語言,語言的意義依附於它被使用的社會情境,因此,除了欣賞魔法帶來的冒險與奇觀,從語言如何被運用並塑造現實的角度來看匡靈秀的小說,也會帶來許多樂趣。
《巴別塔學院》的「銀工魔法」以翻譯過程所失落的意涵作為能量來源,帝國壟斷了銀條,手握翻譯與知識生產的權力,也就主宰世界的意義生成方式;而《地獄修業旅行》的「分析魔法」主要由悖論驅動,設置在大學的分析魔法學系是體制的縮影,上位者主導系統的遊戲規則,盡享研究的果實。
可以這麼說,魔法是一門專業,也是知識與權力的結合,規則可以重寫,只要編織足夠精密的理論就能重塑現實。「以語言重構世界」的信念是魔法的本質,權力也在其中發揮慣性,無論是在帝國、學院,或任何制度裡,那些掌握規則的人,就能定義真理、複製現況,並支配一切。
《地獄修業旅行》故事主角愛麗絲是一位研究生,像許多在學術體制裡打滾的年輕學者一樣,她受到導師的威權與讚美的雙重束縛。導師格萊姆斯是學界的巨人,地位近乎神祇,也代表了學術界道貌岸然、腐敗與掠奪的那一面:剝削研究成果、操控學生,以及以學術理想包裝的權勢。年輕學者一方面對知識尚懷有熱情,追求真理,勉力擠身學術窄門;另一方面也漸漸要招架頭銜、名望與自戀的侵蝕。
這正是愛麗絲在故事中所面臨的困境:她追求認可與成就,又逐漸明白,體系基礎建立在欺瞞與因循。學術的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在地獄具現為貧瘠的沙漠,亦即失去生機的世界。愛麗絲「下地獄」是為了補救錯誤,但究竟該怎麼做才是救援成功?
愛麗絲身上的魔法陣,讓她「無法遺忘」。阿根廷作家波赫士有一個短篇〈博聞強記的富內斯〉,故事記述了從未馴服的馬匹上所摔落的少年。少年自此癱瘓,卻同時擁有了絕佳的記憶力,他能毫不含糊地再現一整天的情況,但每次都需要耗掉一整天。也就是說,當他播放倒轉的過去同時開展未來,然而未來亦是倒回的過去。
導師格萊姆斯在她身上畫下的魔法陣,使愛麗絲從思考的個體,變成了記憶的容器、學術的工具,而身為人,無法遺忘是一種詛咒。無法遺忘,意味永遠活在過去的創傷與焦慮、活在重重疊疊的記憶迷宮,當所有的經驗都被強迫保存,愛麗絲便失去了重新詮釋自我的能力。這個魔法陣,就個人的生命而言是受困於記憶迴圈,遭遇身分逐漸崩解的危機;就系統中達成目標的工具而言,愛麗絲將永遠無法逃離導師格萊姆斯的陰影。
靈魂唯有忘記前世才能轉世,地獄的概念,和愛麗絲的目標可說是背道而馳。翻越沙漠,橫渡「忘川」,愛麗絲原本預計的地獄之旅是要補救把導師炸得支離破碎的錯誤。愛麗絲想要找到好工作,格萊姆斯的威信等於就業保證,而所有格萊姆斯給的苦頭,都證明愛麗絲足夠堅強、值得栽培,她是特別的。許多靈魂在地獄中遲遲不願離開,他們仍緊握某種意義的幻影,愛麗絲這才驚覺,滯留於地獄的靈魂與自己何其相似。執念造就了地獄,不論是大學城的街道與功能性的建築,那些前世地景的海市蜃樓,或一間間無盡重演慾望的房間,乃至於無際涯的沙漠,都一樣的荒蕪。
這也就讓愛麗絲原本要帶回導師靈魂的營救行動,下黃泉的這一遭,反而變成了拯救自己的旅程。不必再從導師的眼中來尋找價值,而是從自身的經驗與信念來重建意義;不再順從權威所打造的遊戲規則,就能解放那個渺小的自己。行動結果沒有帶來英雄式的凱旋,現況和剛下地獄的初始設定相比也沒有顯著改變(儘管支付了一些代價),但她確實變得不一樣了。
魔法的核心是語言,研究語言的悖論,模糊與矛盾並未就此解消,然而思考的邊界會變得清晰。透過檢視邏輯的限制、認知的盲點,會促進對核心觀點的理解。魔法從意志力裡誕生,相信什麼,就可能打造怎樣的世界。辨認悖論的存在、看見對立的信念,才不會被固定框架所侷限,魔法師的力量在於能看見顛倒的世界。「你以為世界是這個樣子的,卻突然發現並非如此。」要練就這樣的眼光,必須放下安全感,看見體制與真理背後的裂縫。說到底,學術追求不正是這樣一種啟蒙的行動嗎?這樣看來,愛麗絲確實挽救了自己的未來。
作者/傅淑萍
現為「我們的教學事業有限公司」講師,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部落格「樂遊原」與IG「樂遊原(@leyou_yuan)」共同經營者。曾任聯合報文學寫作營講師。曾擔任聯合盃作文大賽閱卷與命題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