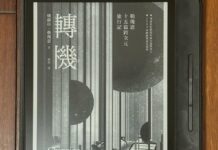- 下班時刻的車廂中擠滿了人,站在我身旁的人橫在我面前的那隻扶著握把的手,只距離我的眼睛不到十公分;而我的鼻尖嗅著前面的女子,幾乎可以從她呼出的。
- 我艱難地撈出大背包裡的書本閱讀,想藉此度過五十分鐘車程裡,和陌生人靠得太近彼此對望的尷尬,但眼神雖落在手中的書頁,耳裡仍擋不住一波波襲來的音。
- 前方座席有兩個五六歲貌似姊弟的小孩,身軀歪倚在媽媽身上,咿咿哦哦地吵鬧拌嘴,不知怎地小男孩突然加大音量對姊姊說:「對不起啦。
- Q:這篇在講什麼?
- A:下班時刻的車廂中擠滿了人,站在我身旁的人橫在我面前的那隻扶著握把的手,只距離我的眼睛不到十公分;而我的鼻尖嗅著前面的女子,幾乎可以從她呼出的。
- Q:重點是什麼?
- A:我艱難地撈出大背包裡的書本閱讀,想藉此度過五十分鐘車程裡,和陌生人靠得太近彼此對望的尷尬,但眼神雖落在手中的書頁,耳裡仍擋不住一波波襲來的音。

下班時刻的車廂中擠滿了人,站在我身旁的人橫在我面前的那隻扶著握把的手,只距離我的眼睛不到十公分;而我的鼻尖嗅著前面的女子,幾乎可以從她呼出的氣息中分辨出她吃了什麼。我艱難地撈出大背包裡的書本閱讀,想藉此度過五十分鐘車程裡,和陌生人靠得太近彼此對望的尷尬,但眼神雖落在手中的書頁,耳裡仍擋不住一波波襲來的音浪。
前方座席有兩個五六歲貌似姊弟的小孩,身軀歪倚在媽媽身上,咿咿哦哦地吵鬧拌嘴,不知怎地小男孩突然加大音量對姊姊說:「對不起啦!」小女孩表情無奈地回:「我又沒有怎樣。」小男孩彷彿不甘心未獲得滿意的答案,跳針般不斷說著「對不起」這三個字;小女孩則甚顯無奈地頻回他「我又沒有怎樣」。他們就這樣僵持不下,直到媽媽出聲對小女孩說:「妳就跟他說沒關係就好了嘛!」小女孩癟一癟嘴:「可是跟他說沒關係就表示我本來覺得有關係,然後他說了對不起我就原諒他了才說沒關係,可是我又沒覺得怎樣,他為什麼要說對不起?我又沒怪他,為什麼要跟他說沒關係?」一時間,我們這些站著聽小女孩說話的大人,彷彿都在等待媽媽的回答,也似乎都在思考:沒關係代表什麼?什麼叫做原諒?
向他人說「對不起」,通常都是因為覺得我們的行為言語不當,讓對方不舒服或權益受損,這三個字說出口時,潛意識裡應該都是希望對方能原諒自己。道歉、抱歉、致歉這幾個詞,都是指懷抱著歉意、自覺有愧而向對方表達心中的歉疚,而賠罪一詞程度更重,已有負罪感了,但這些都是從自已的角度出發。若是由對方的角度來看呢?他不覺得你有錯、不覺得你虧欠自己、更不認為你有罪,那麼何須原諒?你企圖想透過道歉獲致對方的寬恕又從何說起?
魯迅在<風箏>裡曾描述一個請求寬恕而未得的故事。他曾經是嫌惡風箏的,認為那是沒出息的孩子所做的玩意,並對於小他好幾歲的弟弟如此喜歡風箏感到可鄙。因此某天他發現弟弟瞞著他偷做沒出息孩子的玩意時,他毫不猶豫地折斷風箏骨架,擲在地上踏扁它。魯迅用乾脆俐落的筆調寫下那個令人震撼決絕的場景:「論長幼,論力氣,他是都敵不過我的,我當然得到完全的勝利,於是傲然走出,留他絕望地站在小屋裏。後來他怎樣,我不知道,也沒有留心。」
這樣狠心甚至有點殘暴的兄長值得原諒嗎?想必已在弟弟童稚的心中已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多年後魯迅終於意識到自己近於精神虐殺式的行為是種錯誤,他決定去討弟弟的寬恕,等弟弟說「我可是毫不怪你呵」,他負罪的心就能輕鬆了。關鍵的時刻來到,中年的魯迅向弟弟剖白當年殘忍的行為,並等著弟弟那句「我可是毫不怪你呵」一出口,自己卽刻便受寬恕,心也從此寬鬆。但故事的結尾並不是如此,魯迅把那種無法掌握無能為力無可改變寫得精采:「『有過這樣的事麼?』他驚異地笑著說,就像旁聽着別人的故事一樣。他什麼也記不得了。全然忘卻,毫無怨恨,又有什麼寬恕之可言呢?無怨的恕,說謊罷了。我還能希求什麼呢?我的心只得沈重着。」
「無怨的恕」,從對方的角度來說,他根本無怨,甚至不記得了,那麼你非要他給你一個說法以示原諒,這豈非要對方說謊,只為安頓自己的不安、歉意、愧疚與罪惡感?我們要的是他人的原諒,還是自己原諒自己?也許最過不去的其實是自己這一關。
幾年前童書作家羅德達爾的《吹夢巨人》改編成電影時,我帶女兒去電影院觀影。我雖然也被被充滿想像力的劇情吸引,但卻不像孩子般完全投入故事中,而是對一段不起眼的情節印象深刻:巨人們將一個個惡夢裝進玻璃瓶,其中裝著「最可怕惡夢」的玻璃瓶中,有一團鮮紅亂竄、亟欲鑽入人們意識底層的光點。玻璃瓶上寫著這個夢的內容是:「你看看你做了什麼?沒有人會原諒你的。」
這真是最可怕的夢魘--來不及了,你已經做了,做了那件再也無法挽回的事,然後,沒有人要原諒你,一個都沒有!包括你自己!--我想像著那樣一件無法挽回且無法獲得原諒的事。
車廂裡那兩位小姊弟終於安靜下來,在姊姊說了「沒關係」之後。年幼的弟弟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滿意地放過姊姊,但那只是此時,會不會有一天他將發現,原諒自己才是最難的。
作者
水日光